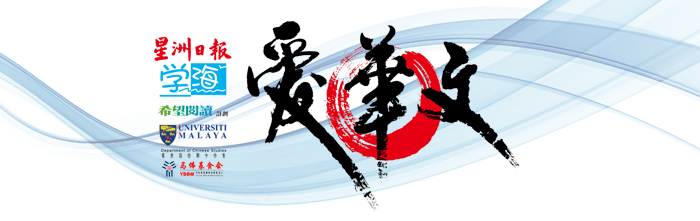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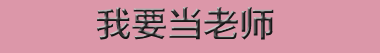
两年前,当我开始教校内报考人数不多的SPM中国文学时,我在第一堂课便问了学生他们报考的原因。我记得那是放学后的下午,校园人去楼空后,我们在一间课室内初次见面。
课室内不到十位的学生大部分回答:“我喜欢华文。”其实,这应该是预料之内的答案,可是当一个接一个学生说喜欢华文,也想好好地读古文时,我的心还是轻易地被触动了。
我怀揣着一份圆梦的心思接下这份工作,因为当我十七岁时,我并不知道SPM有这一门科目,当年的我错过了成为考生,现在的我可以成为考生背后的老师,也算是另一种补偿。只是当我想到我必须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外另外备课,就会觉得自己何苦呢?一直到听见学生说喜欢华文,看到他们纯粹喜欢一件事情的模样,瞬间让我联想到同样喜欢华文的我,于是这工作也成了一件乐事。
或许在以数理为主的学府中,喜欢文学的我们是“怪咖”吧!每一次放学,所有学生都往校门口冲去,老师们也准备下班的时候,这几位学生就来到课室,和我一起读古文。当我们读到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中提及瑰丽奇景通常都会在比较难到达的地方,而这些地方通常都是“人之所罕至”,就会联想到同样走上一段少有人烟之路的我们。借着古文予我们完成理想的力量,每一次上课时间都飞逝而过,当我离开课室,回到安静得让人无所适从的校园时,我才惊觉自己的孤单,便赶紧收拾,走出校园,然而脑海里还是装着刚刚讲的那篇古文,再一次折服于古文的魅力之中。
文学是小众爱好,我在这几个学生组成的小天地里自得其乐。有时候讲到某些段落,我实在无法按捺内心激动心情,抬头看见学生只会狂写笔记,就会反复问学生“为什么”,逼着这些早已习惯靠“背”来考华文的学生放下笔,钻进字里行间内思考,而最好玩的古文莫过于《鸿门宴》。比起其它古文,《鸿门宴》的篇幅很长,我却很喜欢讲这篇课文,作者用精简文字刻画人物、交待故事情节,也多处留白,供读者联想。当我问学生,刘邦麾下猛将樊哙撞倒门外守卫,破门而入时,为何在张良为其道明身份后,项羽即解除警备,还一句句“壮士”,赐他酒、猪腿,又再赐酒?学生会说,那时因为项羽完全相信刘邦毫无与他争霸中原的野心。
我会先肯定学生的答案,但不满足于此,继续追问,“还有吗?”学生就开始摸不着头脑了,我便提示:“樊哙这个人怎么样?”
学生会回答:“直爽男子汉。”
我再追问:“像谁?”
学生这时笑了,我知道他们揭开谜底了,“项羽!”
我会将这段落诠释为项羽通过樊哙的动作与外型,认为樊哙是和他契合的人,就像云云人海中,现实中的我们就是会被某种气质的人吸引那样。紧接着我会再问学生一个问题:“所以啊,谁是真的在开party呢?”以此再带出项羽胸无城府的人物形象,再对比全文最后一句“沛公至军,立诛杀曹无伤”刘邦的果断利落却也心狠手辣。课文结束后,我再抛出最后一个问题:“如果是交朋友,你会选择项羽还是刘邦?”毫无疑问地,学生都选择了前者。阅读历史,一般人会很自然地将成功者等同正面人物,失败者便是负面人物,但通过这样一步步提问,学生也会更能理解作者司马迁将项羽塑造为“悲剧英雄”的同情视角,而我也达到了学生与我在古文中同乐的目的。
比起教学生考得高分的作答技巧,我更愿意做一位经典诠释者,以提问方式,一步步推进,从有形文字到缥缈情感,我就像在汉字迷宫内提灯照耀前方路,待学生一一走过最后一个字,合上课本后,我的眼眸内还留着余光。教书的人总比听书的人学得更多,每一次为了备课再读一次文章,为了陪学生阅读又一字一句地诠释一遍,每一年都读的文章,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所获。我很庆幸自己最终成为了一位华文老师,藉着工作需要,任性地浸泡在一代又一代文人酿造的传世名篇内。
古人把文章写得那么好,快乐学古文才对得起他们。报考中国文学的学生除了喜欢华文外,也有一小部分同学很坦诚地说,他们只是想报考多一科,多拿一个拿A。比起大部分只求及格,安逸过完中学生活的青少年,这群学生已经是志气非凡,我欣赏他们目标明确,但暗地里也希望通过这一年的课程,让他们对“华文”改观,至少不再认为华文只是个拉高学业水平的工具,至少在毕业前感受一次阅读古文的快乐吧。
这几天,新一年的高二学生又要开始报考中国文学了。学校召开说明会的时候,来的人寥寥无几,我还以为今年轻松一些了,怎知一周之内,陆陆续续来了几位学生说自己错过了说明会,便亲自来向我了解课程。这时,即便我已知道答案,但还是想问“为什么要报考啊?”
“因为我喜欢华文啊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