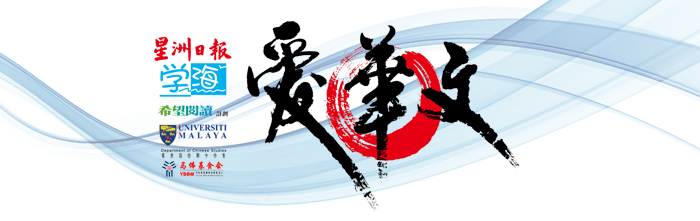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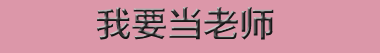
我已经退休五年半,最近读到国中华文班的窘境,想起当国中华文老师的日子,感触良多。
我主要负责教导初中华文,这些班级大都是下午班,华文课安排在课程表外,学生必须提早到学校上课。由于课室不足,我们趁上午班学生去上科学或体育的时候借用课室。除此以外,我们也曾经借用科学实验室、生活技能室、美术室、会议室、家政室、电脑室等地方上课。华文老师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寻找课室。当上述地点都安排不到,食堂成为最后的选择,但那儿连黑板也没有,最不理想。
借用他人之课室,最忌学生偷吃糖果,把糖纸塞进别人的抽屉。有的比较顽皮,擅自翻阅别人的课本或笔记,甚至破坏别人之物。接到那一班学生的投诉之后,我必须找出罪魁祸首,严加惩罚,别让害群之马影响华文班的声誉。当然,那是极少发生的,绝大多数的华文班学生都是循规蹈矩的学生。
某次站在中六理科班的门外,学生出来之后,我们正准备进入,班长突然把课室的前后门都锁了。我们眼巴巴地看他们离开,尽管我以最犀利的眼光瞪着班长,他却若无其事地走了。中六理科班班长,也是学校巡察员,曾经是我负责的某学会理事,他却狠心把我们锁在门外,无视老师及他的学弟妹脸上错愕的表情。那一次吃闭门羹,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屈辱!其实,问题出于那天早上有的空课室发生财物失窃事件,副校长通过广播,通知所有班长,课室内若没人必须上锁,若上锁,她将严惩班长。我也不能责怪班长,他只是遵循副校长的指示,别无他意。后来,我们另外找课室,幸好有一间生活技能室没人,我们才有栖身之处。
生活技能科主任是我的老朋友,借用她的课室上课,我感到毫无压力。刘老师是虔诚的基督徒,与我联手负责学校的学生团契。课室的摆设与普通课室有些不同,黑板与科学室一样,有四个小黑板,必须拉上或拉下。课室摆设六张较大的桌子,可容六人,旁边设有洗手盆。这种课室格式,挺适合进行小组讨论,但是也有弊病,即使没有小组讨论,有的学生还在那儿“讨论”。
学校的会议室也是华文班上课的另一个选择。会议室有冷气设备,在炎热的天气,进入冷飕飕的会议室,感到格外舒适。由于其他老师也常使用会议室,我不能老是安排学生进来吹冷气。会议室有视听器材,老师们可以用电脑播放视频,这是多元化的教学方式,深获学生们的喜爱。记得我曾播放《超级演说家》参赛者刘媛媛的演说:《寒门再难出贵子》。我永远记得她说过:“我们家根本称不上寒门,因为我们家根本就没有门”。她的演说激励人心,听者无不动容。从寒门我联想到文化之门,我感到庆幸,我的学生已经找到那扇通往中华文化之门。
我们经常在科学室上课,特别是物理实验室,那是罗娜老师的地盘。每次在那儿上课,心理压力大,嘱咐学生千万别乱丢垃圾,也别把食物的残渣丢在室内的垃圾桶。多年以前,我也曾经“客串”科学老师。那一年,来了一位马大中文系的毕业生,我这个非中文系出生的华文老师被调去教中五的科学。身为科学组主任,罗娜老师质疑我的教学能力。以国语教中五的科学,对习惯讲中文的老师来说,肯定不容易。她说先给我一段时间适应,然后才进班观察,评估我的教学能力,我听了颇有压力。校长巡课时曾经在走廊驻足聆听我的教学,听我讲得头头是道,我偷瞄他一眼,感受到他对“跨界”老师的肯定。不久,同事廖老师申请长假,建议我去代课,教中三的数学及中四的英文。罗娜老师来不及进班观察,我已经改教数学和英文,她似乎对此事耿耿于怀。那一年,我一再“换角“,校长及其他同事笑称我多重身份。无论如何,我还是最喜欢当华文老师。后来我去报读开放大学的课程,主修中文,才名正言顺地成为华文老师。
除了科学室,早期我也曾经借用美术室上课。负责管理图画室的黄老师非常友善,相当支持华文教育,只吩咐我别让学生触碰那些尚未完成的作品,如粘土雕塑、油画等。我喜欢美术室的环境,中学时代我对美术颇有兴趣,可惜毕业之后便放下画笔,专注写作。文学与美术原是一家,有多位中国作家也是画家,譬如丰子恺、席慕容、冯骥才、刘墉等。黄老师与学生们把美术室布置得很有艺术情调,我一有空就欣赏挂在墙壁上的学生作品。虽非名家之作,将来他们若成为名画家,这些作品的价值也水涨船高。华文班的莘莘学子,也是尚未完成的作品,只要老师们专心培育,有朝一日,他们将成为华文教育的接班人,有的则在其他领域发展,成为国家的栋梁。多掌握一种语言是优势,何况今日中国已经崛起,成为经济强国,华文班子弟,前途哪会比不上别人?
虽然我们没有固定的课室,经常像母鸡带小鸡,游走在课室走廊,但这也不影响学生学习华文的热忱,让我感到欣慰。我相信多年以后,当他们想起中学时代的华文课,即使面对“飘泊“之宿命,也不向现实低头,这是难得的人生经历。经过风雨磨砺的树木,根基更加牢固,长得更加茁壮、挺拔,勇于面对生活中严峻的挑战。
最后,愿以郑燮的《竹石》与华文班师生们共勉之: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“
